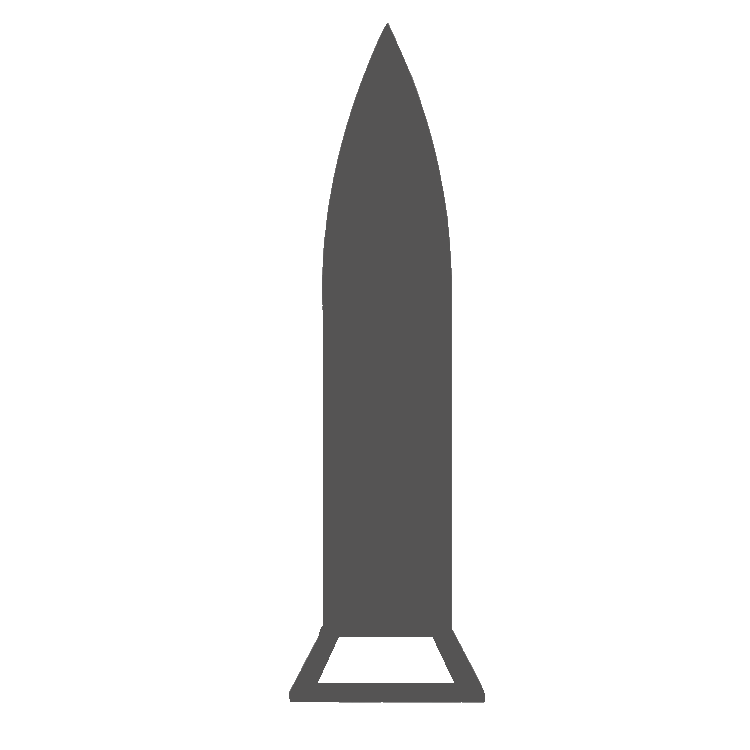作者:林钰源 编辑:博仟雕塑公司
木雕艺术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有“削木象人”的木俑出现。汉代以后木雕技术更加发展,从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木雕作品中,我们看到不仅有造型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有雕刻得相当生动的独角兽、牛、马、羊等形象。
木雕是雕塑的一种,在我们国家常常被称为“民间工艺”。木雕可以分为立体圆雕、根雕、浮雕三大类。木雕是从木工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工种,在我们国家的工种分类中为“精细木工”。以雕刻材料分类的民间美术品种。
从雕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潮州木雕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木雕艺术在明清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在中国雕塑发展史上,关心市井细民的审美要求,表现市井细民为之狂热,为之着迷的内容确具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尽管它是跟随在通俗文学浪潮后面到来,在明清时期整个雕塑艺术特别是那些大型的陵墓雕刻,宗教造像日趋走下坡路的时候,民间雕刻艺术
在雕塑领域的异军突起,给整个雕塑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
“潮州木雕”是明清时期在广东省旧潮州府属九县及福建南部地区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在艺术表现上自成体系的民间木雕种类。它与东阳木雕、黄杨木雕同为这一时期雕塑领域内民间雕刻艺术的重要成就。
关于该地区民间木雕情况,北宋人宋齐古撰山东长清灵岩寺《施五百罗汉记》碑,记中称:“政和(1111-1118年)之初,得官闽中,俗工造像尤为精致。随月所入,食用外,悉付工人成五百罗汉。历水陆五千里至于灵岩。…内辨其质,莫非木雕;外睹其饰,尽是明金。”从这则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到早在北宋政和年间,该地区的金漆木雕已相当精致。宋元时期该地区的木雕现已很难稽考。《韩江闻见录》载有一神话性的用樟木雕刻雨仙像事,与我们目前所见潮州木雕情况相符。直到现在,潮州木雕用得最多的木料仍是樟木。

从目前遗存下来的潮州木雕实物资料上,我们看到除了建筑物的梁拱、柱头、封檐板、退扇(木隔山)、门扇、窗格、门簪等部位多用木雕装饰以外,室内的各式木制家具,如屏风、桌、几、床、椅、叠橱、茶橱纸媒筒、灯芯筒、宣炉罩,以及各种神器和供神器具,如神完、神轿、神亭、围屏、香炉、烛台、香架、撰盒糖枋架、饼架、果碟等都无不饰以精美的金漆木雕不难看出,当时的木雕艺术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只要是用木料制作的器物都与木雕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遗存至今可以确信为明代作品的明代潮州府府衙正门门楼—镇海楼上用以装饰的木猴所看到的雕刻技巧相当可观。镇海楼上的这些木猴,俗称“府楼猴”,当时一共有一百零八只。府楼在辛亥革命时被焚毁,现幸存木猴仅三只。一只为广东省博物馆所收藏,其余二只木猴保存在潮州市博物馆。潮州市博物馆所藏二只形象极为生动,一只双手抱膝,闭目沉思一只左手搂膝,右手挖耳,天真活泼。木猴的雕刻刀法十分圆熟,用刀非常干净利索,力度把握又恰到好处。由于对木猴形、神把握得准确,虽然形体相当简朴而形象却极为逼真,几乎令观者忘却其为木头。
潮州木雕的表现题材十分广泛。有各种图案、花果、禽兽、山水、人物等题材。人物题材除一些表现祥瑞、吉庆的民间传统题材,如《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加冠进禄》等外,大多都取材于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文学名著和地方戏曲。常见的有:《薛仁贵封王》《郭子仪拜寿》《姜尚归周》《渭滨垂钓》《空城计》《长坂坡》《铜雀台》《怒鞭督邮》《刺梁翼》《穆桂英挂帅》《昭君出塞》《蓝关雪》《太白醉酒》《太白醉写》《王羲之爱鹅》《游赤壁》《廿四孝》《西厢》《梁祝》《水淹金山寺》《彩楼招婿》《千里送京娘》《陈三五娘》等。
在考察潮州木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颇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一些严肃的场合如神器、供具,以及宗祠上表现一些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爱情故事,如潮州博物馆藏的一具背面落款“光绪十四年秋月吉立李清合造”的神轿上,就有表现白氏为追求爱情,追求人间幸福在金山寺前同法海展开殊死搏斗的《水淹金山寺》广州美术学院藏的一具神轿上,更有表现潮州地区流传甚广,并一再被潮剧一演再演的《荔镜记》,在一些零散神轿围屏供具以及宗祠上,《唐明王游月宫》《赴彩楼》《仙姬送儿》《陈三五娘》《梁祝》《西厢》等爱情题材更是屡见不鲜。
再看《潮州府志》有载潮州当地迎神赛会的情况“九邑皆事迎神赛会………银花火树,舞榭歌台,鱼龙曼衍之观,蹋跑秋千之技,靡不毕具,故有正月灯二月戏之谚。夜尚影戏,价廉工省而人乐从,通宵聚观至晓方散,惟官长严禁,嚣风斯息。……凡社中以演剧多者相夸耀,所演传奇,皆习南音而操土风,聚观昼夜忘倦……又竟以白镪青蚊掷歌台上,贫者辄取巾帻衣带便面香囊掷之,名日丢采。”这里明白告诉人们,当时人们在迎神赛会活动中所热衷、着迷的绝非是那些呆板、单调、乏味、严肃的宗教仪式,而是当时市井细民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各行业艺人们竞献技艺,他们的创作活动远远跳出了“敬神的范围。正是由于艺人们的创作不是以“神”为中心来进行创作,而是以“人”、以观众为中心来进行艺术创作,因此他们的创作活动虽然远远超出了“敬神”的范围,不仅不被社会所指责,相反地,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欢迎。这一点大概就是潮州木雕中表现内容上的深刻的人民性的所在。
潮州木雕不仅在内容上与潮州戏关系相当密切在艺术表现上,受其影响也颇深。民间艺术总是善于向一些姐妹艺术吸取营养。潮州木雕除了向石雕、泥塑、嵌瓷、纱灯、剪纸、绘画等姐妹艺术学习之外尤其从地方戏曲中吸取了不少营养。潮州戏在潮州木雕艺术表现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它对潮州木雕艺术表现的启迪和影响,在现存潮州木雕作品中是有迹可寻的。
在潮州木雕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潮州戏的脸谱、髯口、行头,甚至舞台上塑造人物形象中常用的一系列程式化了的表演动作,如亮相、捋须甩袖动作、水袖的处理手法等,连舞台处理上的一些虚拟手法都可以在潮州木雕作品中找到。潮州博物馆藏的一件《薛仁贵封王》的木雕作品,描写薛仁贵昔日好友王茂生夫妇以水代酒前来庆贺的“王茂生进酒”的情节:王茂生夫妇见薛仁贵侍从欲去开启酒盖,一时陷入慌乱之中,王茂生双手前伸俯身想去捂住盖子,其妻被吓得慌忙躲往柱子后边。作者在处理这一富于戏剧情节的场面上,无疑从潮州戏那里吸取了一些塑造人物形象的经验,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潮州木雕作品中简直是举不胜举。
潮州木雕在发挥有限的画面空间来表现广阔的生活空间上,更成功地吸取了戏剧表演中的空间虚拟手法。陈少丰老师在《潮州木雕的艺术特色》一文中对这一点论述道:为了在同一装饰木雕版面上展现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故事发展的来龙去脉,常把不同间,不同空间的事物,全都拉到前景上来,变“暗场为“明场”,情节、场面之间,只以简单的树石、门墙相隔,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视觉和联想作用,从而显示出故事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时间先后和主次关系来。如一方“中横肚”上的通雕《七贤进京》,作者充分发挥了通雕这一木雕艺术的特长。所谓“七贤”是传说古代潮州地方的七个书生一道进京应试,一榜题名的事迹。图中七个书生各有一个挑担书筐行囊的僮仆相从。在横长的构图中,右手一座拱桥,左端是道山谷,远处城门在望,中部置一座凉亭。
此外,有几株梧柳,纤曲小径穿插点缀其间。“七贤”及僮仆全部“登场”,有的刚刚从右侧转过山脚出现有“画面”上;有的骑马在过桥:有的坐在凉亭下小憩:有的则进入山谷向城门方向走去。人物之间的距离远不过寸许,立足点虽略有高低不同,但几乎没有远近大小的区别,似乎是旅途中的一个瞬间摄影,但在感觉上,图中的一块岩石、一株小树、一轿、一亭以及路径的转折起伏,却概括了南北数千里,旅途几个月的空间、时间推移变化的全过程。人物走过一座小桥、亭子下的片刻休息,以至手一扬鞭身子一转,体现着他们披星戴月、餐风露宿的旅途生活,颇有绘画上“咫尺千里”和戏曲舞台上“六七步四海九州”似的艺术效果。
潮州木雕虽然十分注意借鉴其他种类的艺术,但绝对不是盲目的模仿,它对戏剧表演程式的吸收和对戏曲表演虚拟手法的借鉴也都不是盲目的。在对待戏曲虚拟手法上,潮州木雕就扬弃了戏曲表演中对各种车、骑、舟、轿以及河流、村庄道路的虚拟,而是直接“牵牛上戏台”。《闵子御车》中的车、《铜雀台》中的坐骑、《游赤壁》中的舟在戏曲表演中无疑都只能是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示,而木雕则是以直接描写的手法来表现。它在吸取其他姐妹艺术的长处的同时没有忘记发扬自身的长处。在人物塑造上,潮州木雕虽然吸收了不少戏剧表演程式,但它同时又不受表演程式的限制。因此,在潮州木雕作品中,我们既可看到戏曲舞台上的各种行当形象,同时也可看到不少生活气息十分浓厚的人物形象。由于潮州木雕的创作自始至终都考虑到观众,它是诚心想让人们看懂,因此它不仅自然地赢得了观众,而且使它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扎下深根,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
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胡人学的。马和胡人,在汉人心目中,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彼此成为种标志和象征。如同西方19世纪油画中习惯以黑奴来渲染、衬托东方情调一般,胡人成为驯养马的代表。渭北的村民也愿意以和马有着亲密感情的胡人来代表种意义和情趣,希望用他们能震慑住马。而狮的形象自从汉代传入中国便一直是种神兽,它往往肩负着守护的重任。这样又有胡人,又有瑞兽,马的主人尽可放心,高枕无忧了。
在狮足或人臂间镂凿出的,用以穿系缰绳的孔洞,则是在浑厚背景上涂的一抹亮色,让人很容易联想起享利·摩尔的雕塑,透明空灵。随着这些孔洞的呼吸,雕像仿佛也被注入了一股活力。狮子们沉着地探出它的前腿,而猴和猎鹰则不安地四下顾盼。
桩颈为顶和身之间的联结部,常处理为双层。上层作圆台形、带四柱的阁形或花瓣形,以承托主体造像;下层常在方柱体上划分出装饰带,通常浮雕一些轮廓模糊的马、羊和鹿。这样一件并不复杂的作品,却集圆雕、线刻、浮雕于一身,也可以称为手法多样了。作为民间艺术,由于题材、用途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几百年来并未使栓马桩造形和内容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而沿续成为其传统。自民国初年以后,民间便不再制作栓马桩了。
经过一段对民间美术的狂热之后,对于栓马桩,人们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很多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它,甚至在《雕塑史》《美术全集》中都只字未提,如此精彩的艺术品,如此待遇,确实让人惊讶和不安。
对于栓马桩,我们不应只着眼于它本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应体会它那种文化精神,如同正负形空间的处理,正形之外的负形,往往更有魅力。如果一件作品有十分气势,精雕细刻了七分,那么人们可以领会的也只有三分了。而栓马桩只用了三分的造型手段,却表现了七分气势,它的精彩也许正在于所塑造形象的似与不似之间,那种生机和神气并未被限制在精确的外形中,而是自由地游离于形象之外,洋溢弥漫在四周。作为用具,它们无疑是简单的,甚至有些粗糙,既使不和富贵华丽的宫廷艺术相比,它们也不免有些简陋。但人的感觉是由粗糙、模糊逐渐向精密、清晰变化的。一件作品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相似的,但随着感觉的细腻化,个人主观成份的增多,便如歧路之羊,不尽相同了。而栓马桩可以让人延长那种粗线条的印象与感觉,让人欲罢不能。
在我国雕塑史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宋之后,雕塑便失去了汉唐那种气魄;但假如我们面对和霍去病墓石刻何其相似的栓马桩,汉唐遗风则扑面而来。
静静的凝视栓马石。因它那种单纯而执着的存在,便足以打动我们了。
如您对潮州木雕与雕塑的关系感兴趣,可继续跳转了解博仟雕塑厂其他文章。